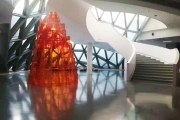我的全部猜疑都在追趕那匹遠(yuǎn)去的白馬,我的全部困惑就像躺著的男人那樣充滿睡意。我所熟悉的蘇新平突然變得陌生起來,仿佛心理相距得無限遙遠(yuǎn)。
頓時我又有了另一種感覺。
那匹白馬一往無前地走向神秘,而那個男人只有夢境。也許我總是負(fù)擔(dān)著猜疑和多思的幾分沉重,我的疲憊我的困惑我的睡意才促成了我的夢境。夢境有時是清醒的極端反動。我卻在夢中自由自在,但也隨時躲避瞬間的驚嚇,擔(dān)心被什么喚醒。這很可能是理論癖與思辨癖的最明確的縮影與象征。而畫家畢竟是畫家,無須在夢中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向神秘。
我的感覺還在繼續(xù)跳舞。顯然這是一種精神的自我運(yùn)動,無需畫家應(yīng)聲而起。我總覺得這畫中有值得勞神去猜度的內(nèi)涵,那神秘的引力時時在起作用。這畫驀地讓我覺得與實際的畫家本人更加隔膜,好像蘇新平一下子成了外星人,我們又偶然相會于一個互不熟稔的新星座。
我開始讀他的畫論。
"在《躺著的男人與遠(yuǎn)去的白馬》一畫中,一匹緩慢走向畫面深處的馬象征著蒙古族牧民那與四時并運(yùn)的生活或勞動,無盡延伸的馬樁乃是其歷程的標(biāo)志,畫面下方躺著的人象征著無為的自然意識,思辨在睡,夢境亦不存在,人與天地的冥合卻是人自身的狀態(tài),這不免有些傷感。"原位的蘇新平努力要說清他作畫的初衷,像一個神話傳說的原型在自我申述,要與任何變異的理解奮力抗?fàn)帯J潞笞髡咭舱f:"我曾多次試圖解釋我的作品,結(jié)果我發(fā)現(xiàn)解釋作品遠(yuǎn)比再畫一幅要難得多。因為它根本就無法解釋。"記得徐冰曾說過:"作品交給社會如同把生靈趕入市場,它已經(jīng)不屬于作者自己了,它屬于所有與它接觸的人。"作品問世后免不了一任人們作精神上的切割。我開篇的臆想歷程就是如此。
不僅僅在這幅畫里,在其它作品中也是如此:他所畫的那些人讓我想起恩斯特·卡西爾關(guān)于人是"符號的動物"的說法??陀^地看,他創(chuàng)造的那些人本身已不具有對象自身的特點(diǎn)。但我還是對蘇新平原意的申述感興趣。"他們的大部分時光是在沉默寡言的孤寂狀態(tài)中度過的,歡騰和奔放乃是這一大的心理狀態(tài)的一種補(bǔ)償和平衡。"其實,蘇新平所表現(xiàn)的人的孤寂并不限于大草原上的孤寂,也含有工業(yè)文明中的城市的孤寂,也是潛在無形的他自己的孤寂。在蘇新平的眼里,人是孤寂的符號!他所創(chuàng)造的白馬,也有同樣的意義,都是孤寂的符號。在這個意義上借用古代哲學(xué)家的話,那就是"白馬非馬"。
蘇新平的畫距離他那原位的表述已經(jīng)相當(dāng)遠(yuǎn)了。我能從他那潛伏著總結(jié)意識的話中強(qiáng)化這種感覺。"回顧這些年的作品,我發(fā)現(xiàn)幾乎全都運(yùn)用了強(qiáng)烈的光,最初并不是有意識地這樣做,只覺得畫面的效果很好看。后來多次去草原,漸漸發(fā)現(xiàn)強(qiáng)烈的陽光常常給我?guī)硪环N莫名其妙的錯覺,有暈眩、有虛幻,世界是凝固的,是不真實的,隨之而來的也有神秘和恐懼。一種體驗一次次重復(fù),慢慢就很自然地出現(xiàn)在畫面中了,并且是有意識地去做了,也終于感到這正是我尋找的,是我需要的東西。"他把對草原人的客觀認(rèn)識只作為一種不重要的精神因素殘留在作品中,更多的空位已被無形的自我意識充分占據(jù)。他與人的距離感是比較含蓄的,表面上的隨和又使他的確定性格具有了矛盾。他那沉靜的固執(zhí)卻在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上幫了他很大的忙,外觀上的若有所思總是躲避挑剔的暗潮。
蘇新平作品中最舒服的狀態(tài)就是生命的靜態(tài)。遠(yuǎn)去的白馬的確不具有"去"的表現(xiàn),卻與四周的五個拴馬樁具有對等的豎立感,這是一種有著"行走姿態(tài)"的靜止感。這是一匹駿馬的假象,那種"行走姿態(tài)"仿佛凍結(jié)在空氣中。蘇新平毫無表情地向我們講了一個沒有邏輯連帶關(guān)系的故事,不知是他把其中的含義和寓意人為地抽空了,還是在主觀表述一個線索的時候無意中又讓最初的思路走失了。我很喜歡目前的格局,即使對畫家一般的創(chuàng)作心理曾經(jīng)感興趣的我,也故意不去看這幅畫的原始草圖。
蘇新平把他主觀上的草原狀態(tài)與城市狀態(tài)以一種"心力"疊壓在一起,當(dāng)然這已遠(yuǎn)遠(yuǎn)超過了加法的魅力。更重要的是他把自我狀態(tài)也實實在在地疊壓在一起。他是一位來自內(nèi)蒙古的青年畫家,并非蒙古族,只不過是在靜觀經(jīng)驗過了的生活。另一方面,他是以城市狀態(tài)在靜觀草原狀態(tài)的,他又是以個人特有的沉靜的固執(zhí)去觸碰生活中的孤獨(dú)感。他故意把畫的背景處理成虛假的空間,非常平面化,任其單純而又冷凝。它是虛假的而又是無限廣大的神秘空間。盡管人、馬、樁都是作為有透視關(guān)系的實體來安置的,但斜射的光線也無法真的把我的直感全然拉回到與記憶相關(guān)的生活中。
在這幅畫中,天、地、人、馬都處在毫無干系的分裂狀態(tài)。這并非是從傳統(tǒng)的文學(xué)性和故事性角度來看的。偶然的物象并置于一個永遠(yuǎn)都不存在的空間里,但那卻是畫家真實的精神空間。按畫家的說法大概是"想象空間"與"物質(zhì)空間"的綜合:
物質(zhì)空間指人們的視覺所及的實景。當(dāng)這種實景轉(zhuǎn)化為繪畫圖像時,就產(chǎn)生了一些方法和規(guī)則,如近大遠(yuǎn)小、近實遠(yuǎn)虛等等,我國宋代畫家郭熙提出的"三遠(yuǎn)"透視法也是一種觀察方法。西方的焦點(diǎn)透視和中國的散點(diǎn)透視都是某種習(xí)慣性的規(guī)則和方法,我們不能判定哪一個更真實。想象空間是一個不受瞬間視覺觀察所約束的再造空間。這種再造空間又分為主動的再造空間和被動的再造空間兩種,被動的如夢境、幻覺等,主動的再造空間是人們有意拼裝、虛構(gòu)的空間。一般來說,繪畫的空間離不開物質(zhì)空間和想象空間,只是側(cè)重點(diǎn)不同。沒有物質(zhì)空間不容易引起和刺激觀者的想象,而沒有想象空間的陌生和迷惑也會使物質(zhì)
空間顯得蒼白乏力。
難怪作者有次說:"一天中我最喜歡黃昏,夕陽下的一切那么單純、寧靜、美好,萬物是凝固的、永恒的。"總之,在對自己的總結(jié)中,畫家還是很理性的,努力用概念來表達(dá)自己。他沒有回避純技術(shù)性的問題,如空間問題。也不在瑣碎的地方浪費(fèi)自己的注意力。在繪畫上,表達(dá)簡捷、單純,而又明確,因此也沒有必要向別人一再說:"我不是這個意思,而是那個意思。"這方面的輕松,他自己感受得也十分明顯。"我發(fā)現(xiàn)同自己交談,同作品交談是那樣地隨心所欲,既準(zhǔn)確,又明白,于是我開始同每一筆、每條線、每個畫面交談了。"
但他的勞頓顯然表現(xiàn)在為排遣孤獨(dú)感而作的堅定的努力上。盡管他已深知?dú)g騰和奔放是對于沉默寡言的孤寂狀態(tài)的一種補(bǔ)償和平衡,但他自己并沒有在表層生活做出瞬間的"如火如荼"狀。畫中的精神狀態(tài)仍是實際的他自己,野性與他隔水相望,爽朗的笑聲并不在他心中脆響。他也"耐慣了孤寂"、"慢慢品味孤寂"。如果說他理解的蒙古族有"對自然的順化意識"的一面,而他自己卻對自我的孤寂有著十足的"順化意識"。他努力去解答物質(zhì)空間里的生活,其實是想解答想象空間中那個無形的自我。我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感受:
我一直試圖用我能理解的、我認(rèn)為最適合自己口味最富表現(xiàn)力的形式來表達(dá)我的感受。通過審視自己最初的作品,通過長期摸索和積累,我似乎發(fā)現(xiàn)了自我,或者說發(fā)現(xiàn)了自己的藝術(shù)個性,我曾努力追求和嘗試的各種形式可能就是今天這個樣子。
我走了一個圓圈。我所熟悉的蘇新平原來是一個正在尋找最適合自我表達(dá)方式的蘇新平,而這個與我心理距離很遠(yuǎn)的陌生的蘇新平才是真正的他。因此,他今天的作品就顯示了更確定的意義。在天地人中,人若不能與天地溝通,那自然是很孤寂的。在具有孤獨(dú)感的人群中,人與人之間不能溝通,則更強(qiáng)化了個體的孤寂。不知是誰說的:"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大于人與猴子的差別。"這種暗潮正在流動,于是不知不覺就把"同聲相應(yīng),同氣相求"歸入古典的幻夢之中了。那個說"天是我的衣服,屋是我的褲子"的裸人是否就不孤獨(dú)了呢?
白馬走了,孤零零地走了,也許會消失于虛無之中。天、地、人,還有拴馬樁都沉靜得讓人難以忍受,非常孤立地存在于一個再造空間中,又把蘇新平要說的話說了個夠!